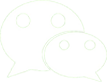发布时间:2024-12-19 浏览:222次
大量研究表明,SCFAs 与精神分裂症的发病及精神分裂症超高危人群的转归有关。目前精神分裂症发病机制的假说中包含五羟色胺假说、谷氨酸假说及神经发育假说,肠道 SCFAs 参与多种神经递质的生成,从而可能与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有关。
1 短链脂肪酸介绍
短链脂肪酸(short chain fatty acids,SCFAs)指碳原子数不超过 6 的有机酸,主要包括乙酸、丙酸、丁酸、异丁酸、戊酸、异戊酸和己酸,是大肠微生物代谢的主要终末产物之一。
因为肠道包含人体中最多的微生物群,这些微生物通过发酵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肽和糖蛋白前体等这些难以消化的大分子参与人体代谢过程,产生短链脂肪酸及其它代谢产物。
肠道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又受众多因素的影响,例如肠道运输时间、饮食、温度、pH、老龄化、神经内分泌、药物等,因此短链脂肪酸的产生、数量、比例也会随着这些相关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短链脂肪酸在大肠近端的含量最高,结肠中乙酸、丙酸、丁酸的含量比也约为 3:1:1 [1] 。SCFAs 的代谢也有区别:70%~90%的丁酸在结肠被消耗为能量来源,乙酸和丙酸大部分被运输至门静脉,而丙酸在门静脉处通过糖异生被肝脏代谢后,乙酸成为外周血中剩余浓度最高的酸。
2 SCFAs的生理作用
SCFAs 主要通过与 G 蛋白耦联受体结合在人体内发挥作用。能与 SCFAs 结合的受体主要包括G 蛋白偶联受体 43(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43,GPR43)、GPR41、GPR109a。这些受体在人体大部分组织中均有分布,其中 GPR41 主要分布在脂肪组织,GPR43在免疫细胞中高表达,二者都能与乙酸、丙酸、丁酸结合,而 GPR109a 则主要表达于脂肪组织和免疫细胞,且只能被丁酸盐激活。
SCFAs 具有各式各样的生理作用,例如乙酸不仅能作为周边组织能源物质,调节脂肪细胞分化,还能合成长链脂肪酸、胆固醇、谷氨酰胺、 β - 羟丁酸等物质。丙酸能作为糖异生的底物,降低胆固醇活性,刺激瘦素增长;丁酸是结肠、盲肠的主要能量物质之一,异己酸是肠道微生物组成受损的标志[2]。
目前对 SCFAs 作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抗炎、免疫调节、维持 HPA 轴稳定、维持肠上皮细胞完整性及抗肿瘤上。研究表明,大部分 SCFAs 可以通过与 GPR41和 GPR43 受体结合发挥抗炎作用。人体血液循环中,高水平含量的 SCFAs 可以缓解人体炎症。有研究发现,GPR43 -/- 小鼠更容易被右旋糖酐硫酸钠或三硝基苯磺酸诱导产生结肠炎症反应 [3] 乙酸可以抑制右旋糖酐硫酸钠诱导无菌小鼠结肠炎症的产生,但对 GPR43 -/- 小鼠效果不佳 [4] 。部分 SCFAs 如乙酸、丁酸可以作为组蛋白脱乙酰酶 -1((histonedeacetylase,HDAC-1)抑制剂,影响海马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表达水平[5],抑制小胶质细胞的激活。
但并不是所有 SCFAs 都具有抗炎作用,研究发现丙酸能破坏神经递质的生成,并能激活小胶质细胞[6]。SCFAs 主要通过两种机制在免疫调节中发挥作用。第一,SCFAs 作为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显著影响 Treg 细胞的增殖发育及迁移能力,发挥免疫抑制功能,例如丁酸盐能促进 M2 巨噬细胞活化。第二,SCFAs 通过与 G 蛋白耦联受体结合,抑制中性粒细胞趋化、增加抗炎分子的表达,影响 Treg 细胞的增殖发育和炎症介质的募集 [7] 还能调节固有巨噬细胞 - 小胶质细胞的分化和功能维持中枢神经系统免疫稳态 [8] 除以上两种机制外,SCFAs 还能通过 Ca2+ 动员介导白细胞激活,丁酸也介导肠道免疫球蛋白 A(Immunoglobulin A,IgA)的分泌增强粘膜免疫功能。因此,SCFAs 在应对急性和慢性炎症的免疫调节作用上是必不可少的。
SCFAs 在维持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轴(The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HPA)稳定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乙酸、丙酸、丁酸能跨越血脑屏障,通过调节神经 - 内分泌系统,缓解 HPA 轴亢进,减轻心理应激诱导的行为改变。Gagliano 等[9] 的研究表明,SCFAs 可以降低促肾上腺皮质素释放激素(cortic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CRH)水平,但高水平(1200 mg/kg)丁酸可以引发压力应激,显著提高血浆中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dreno-cortico-tropic-hormone,ACTH)。
除抗炎、免疫、维持 HPA 轴稳定外,SCFA 在维持肠上皮完整性、抗肿瘤上也起着作用。肠道中的 SCFAs 可以间接刺激维持肠道上皮细胞完整性的关键因子 IL-8 表达 [10] 。丁酸不仅能介导肠道分泌 IgA 维持肠上皮完整性,还能通过 AMP 激活蛋白酶(Adenosine 5-monophosphate(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e,AMPK),改变紧密蛋白的连接,从而保护肠道上皮屏障。
然而,不是所有的 SCFAs 对肠道都起保护作用,丙酸能刺激双歧杆菌属的生长,从而增加肠道屏障的通透性。在抗肿瘤方面,SCFAs能通过维持细胞分裂与凋亡的平衡,抑制肠道和局部淋巴结中炎性免疫细胞的发育、分化或聚集,从而起到抗肿瘤效应[11]。
3 SCFAs与肠- 脑轴
随着微生物 - 肠 - 脑轴研究的深入,已有大量研究证明微生物肠脑轴和中枢神经系统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目前公认最主要的通路有四条:迷走神经通路、免疫通路、神经内分泌通路和代谢通路,不同通路之间可以相互影响。
SCFAs 作为肠道微生物代谢的重要终末产物之一,能够直接或间接参与各个通路的调节。在迷走神经通路中,SCFAs 主要通过与交感神经系统中高表达的 GPR41 结合,对肠道中广泛分布的迷走神经起抑制作用;在免疫通路中,SCFAs 可作为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或通过G 蛋白耦联受体信号转导通路发挥免疫调控功能;在神经内分泌通路中,SCFAs 也能通过影响 5- 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e,5-HT)和多巴胺等神经递质的分泌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研究发现,肠道中5-HT 随 SCFAs 的减少而减少,乙酸、丁酸、异丁酸能间接促进 5-HT 的生成[12] 。
最后,在代谢通路中,SCFAs 本身作为肠微生物的终末代谢产物之一,通过结合 3种G蛋白偶联受体发挥神经活性作用。
4 SCFAs与精神疾病
因 SCFAs 能作用于微生物 - 肠 - 脑轴并且能通过血脑屏障引发大脑中免疫炎症反应的特性,近些年来,关于 SCFAs 对各类精神系统疾病影响的研究逐渐展开。大量研究表明,SCFAs 与精神分裂症的发病及精神分裂症超高危人群的转归有关。
目前精神分裂症发病机制的假说中包含五羟色胺假说、谷氨酸假说及神经发育假说,肠道 SCFAs 参与多种神经递质的生成,从而可能与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有关。例如SCFAs 可以刺激肠道内分泌细胞分泌组胺、血清素、5- 氨基戊酸和丁酰氨基丁酸等。有研究认为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粪便总 SCFAs、乙酸、异戊酸和己酸水平高于正常人,异丁酸水平低于正常人 [13] 。Zhu等还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 SCFAs 越高认知功能损害越严重。在动物实验中,Zhu 还发现摄入过量短链脂肪酸会诱发小鼠的精神分裂症样行为 [14] 。
在精神分裂症超高危人群中,贺莹等 [15] 对精神分裂症超高危人群的微生物群落特征进行预测,发现 SCFAs的合成通路——丙酮酸合成、乙酰辅酶 A 合成及脂肪酸的初始合成通路较对照组有明显激活,精神分裂症超高危人群肠道中含有更高水平的产丙酸菌 clostridia,既往也有研究证明超高危人群粪便中Clostridiales 和 Prevotella 升高,都是肠道中产 SCFAs的主要菌种。
在抑郁症患者中,SCFAs 可以通过影响 HPA 轴稳定性影响抑郁症的病程。大部分抑郁症患者都伴随 HPA 轴亢进的现象,而 SCFAs 可以通过神经内分泌通路缓解 HPA 轴亢进。如 5-HT 是抗抑郁的重要神经递质,乙酸、丁酸可以促进5-HT的生成,抑郁症患者体内乙酸、丁酸含量都降低,以致 5-HT 的生成不足,同时,因乙酸也可被产丁酸的细菌利用生成丁酸,所以抑郁症患者体内丁酸含量的降低可能与乙酸含量不足有关。
近些年来有提出粪便微生物群移植治疗抑郁症的方法,有学者认为该理论的提出可能与 SCFAs 有关。有研究发现,对一个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进行多次粪便微生物群移植治疗,同时停止药物治疗,患者的抑郁症状在 6 个月后消失,躁狂症状在12个月后消失[16]。
SCFAs与自闭症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多。研究发现,母孕期暴露于丙戊酸盐的胎儿出现自闭症样行为的风险增高 [17] 。
无菌小鼠缺乏正常的肠道微生物组合,会产生躲避其他小鼠,回避社交行为的现象,推测与无法产生适当组成的SCFAs有关,同时,过量摄入丙酸也会在老鼠身上引起类似自闭症的症状,比如重复的兴趣、特殊的动作和不典型的社会互动。
目前对自闭症患者粪便 SCFAs 含量变化研究存在争议,Simeng Liu 等研究发现,自闭症患者粪便中乙酸和丁酸水平较低,戊酸水平升高,从而提出戊酸是自闭症的另一个相关因素,也有研究结果显示,自闭症患儿粪便中SCFAs总量显著增加,乙酸、丁酸、戊酸和异戊酸浓度升高,己酸浓度降低[18]。
5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SCFAs 的作用涉及抗炎、免疫、维持HPA轴稳定等多方面,其主要的成分乙酸、丙酸、丁酸的含量和比例变化与精神系统疾病关联密切。
目前,SCFAs 与精神系统疾病的研究相对较少,结论各异,因此,进一步研究 SCFAs 在精神疾病中的作用能够为我们深入了解精神疾病、改善治疗及预后提供新的线索。
#参考来源#
1. Ganapathy V,Thangaraju M,Prasad PD,et al. Transporters and receptors for short-chain fatty acids as the molecular link between colonic bacteria and the host[J]. Current Opinion in Pharmacology,2013,13(6):869-874.
2. Kang YB,Cai Y,Zhang H. Gut microbiota and allergy/asth-ma:From pathogenesis to new therapeutic strategies[J]. Aller-gologia et Immunopathologia,2017,45(3):305-309.
3. Maslowski KM,Vieira AT,Ng A,et al. Regulation of in-flammatory responses by gut microbiota and chemoattractant receptor GPR43[J]. Nature(London),2009,461(7268):
1282-1286.
4. Sivaprakasam S,Prasad PD,Singh N. Benefits of short-chain fatty acids and their receptors in inflammation and car-cinogenesis[J]. Pharmacology & Therapeutics,2016,164:144-151.
5. Martins-de-Souza D. Proteome and transcriptome analysis sug-gests oligodendrocyte dysfunction in schizophrenia[J].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2010,44(3):149-156.
6. Sherwin E,Sandhu KV,Dinan TG,et al.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The Light and Dark Sides of the Microbiota–Gut–Brain Axis in Neuropsychiatry[J]. CNS Drugs,2016,30(11):1019-1041.
7. Ang Z,Er JZ,Ding JL. The short-chain fatty acid receptor GPR43 is transcriptionally regulated by XBP1 in human mono-cytes[J]. Scientific Reports,2015,5(1):8134.
8. 喻志敏,吕亚楠,刘雅微,等 . 短链脂肪酸的免疫调节机制及其与多发性硬化的关系[J]. 脑与神经疾病杂志,2020,28(01):65-67.
9. Gagliano H,Delgado-Morales R,Sanz-Garcia A,et al.High doses of the histone deacetylase inhibitor sodium butyrate trigger a stress-like response[J]. Neuropharmacology,2014,79:75-82.
10. Macia L,Tan J,Vieira AT,et al. Metabolite-sensing re-ceptors GPR43 and GPR109A facilitate dietary fibre-induced gut homeostasis through regulation of the inflammasome[J].Nature Communications,2015,6(1):6734.
11. Ma H,Yu Y,Wang MM,et al. Correlation between mi-crobes and colorectal cancer:tumor apoptosis is induced by sitosterols through promoting gut microbiota to produce short-chain fatty acids[J]. Apoptosis,2019,24(1-2):168-183.
12. Bellono NW,Bayrer JR,Leitch DB,et al. Enterochromaf-fin Cells Are Gut Chemosensors that Couple to Sensory Neural Pathways[J]. Cell,2017,170(1):185-198,e16.
13. 李慧慧 . 肠道菌群及短链脂肪酸与精神分裂症的相关性研究,2020,郑州大学.
14. Feng Zhu,W. W. Q. M. Role of short-chain fatty acids in the gut-brain axis in schizophrenia[J].2020.
15. He Y,Kosciolek T,Tang JS,et al. Gut microbiome and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study of subjects at ultra-high risk for psychosis may support the membrane hypothesis[J]. European Psychiatry,2018,53:37-45.
16. Hinton R. A case report looking at the effects of fa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in a patient with bipolar disorder[J]. Aust NZJ Psychiatry,2020,54(6):649-650.
17. Smith V,Brown N. Prenatal valproate exposure and risk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nd childhood autism[J]. Arch Dis Child Educ Pract Ed.2014,99(5):198.
18. Vuong HE,Hsiao EY. Emerging Roles for the Gut Microbi-ome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J]. Biol Psychiatry,2017,81(5):411-423.
#酒局守护神 #酉神1号 #酉神一号 #酉神壹号 #酒神1号 #酒神一号 #酒神壹号 #酉神1号解酒液 #酉神1号有机酸解酒液